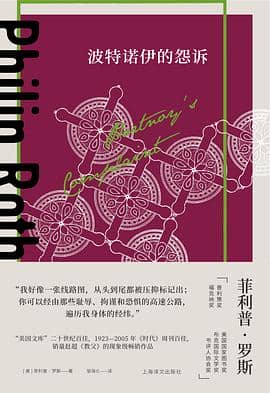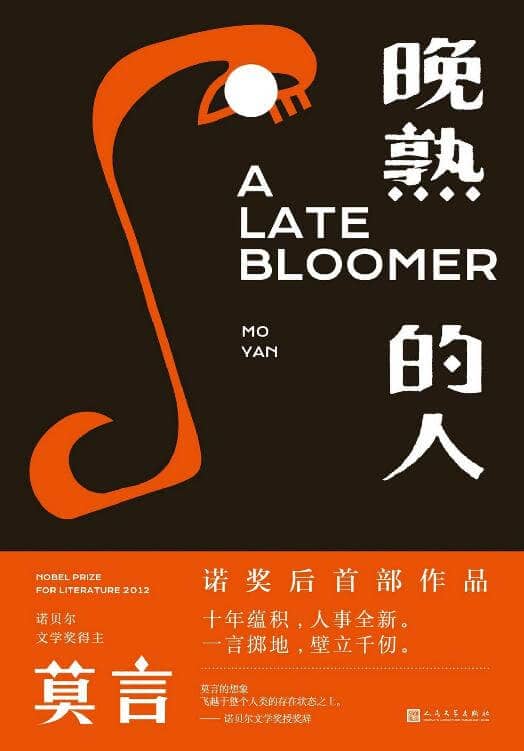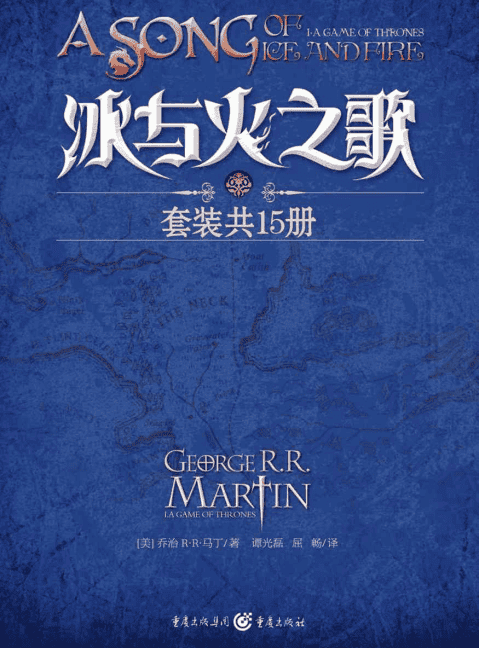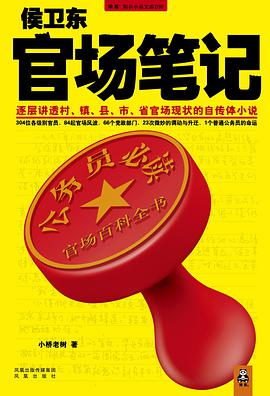内容简介:
* “美国文库”二十世纪百佳,1923—2005年《时代》周刊百佳,销量赶超《教父》的现象级畅销作品
* “我好像一张线路图,从头到尾都被压抑标记出;你可以经由那些耻辱、拘谨和恐惧的高速公路,遍历我身体的经纬。”
《波特诺伊的怨诉》是菲利普•罗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,也是一部话题之作。1969年甫一推出,便引起轰动并长居畅销榜,销量甚至超过了同年出版的《教父》。后入选”美国文库”20世纪百佳,1923-2005年《时代》周刊百佳。有评论称,该小说同索尔•贝娄的《赫索格》一道,定义了1960年代的美国犹太文学。
故事发生在心理医师施皮尔福格尔的躺椅上。主人公波特诺伊饱受神经官能症的困扰,他找到心理医师施皮尔福格尔,向他倾诉自己从小到大所面临的困境:父亲望子成龙的期待、母亲专制霸道的溺爱、犹太身份的困扰……
大胆而近乎荒诞的告白背后,暗含的是他那一代美国犹太青年内心的道德焦虑,是传统的犹太道德意识与60年代美国社会自由意识之间的冲突、失衡,也是美国犹太人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生存焦虑。
作者简介:
菲利普•罗斯(1933-2018)
美国小说家,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。1959年凭借处女作《再见,哥伦布》受到瞩目,此后笔耕不辍,获奖无数,赢得国内外的高度认可。2012年宣布封笔,一生共创作29部小说,代表作有《波特诺伊的怨诉》《鬼作家》《萨巴斯剧院》《美国牧歌》《人性的污秽》等。
试读:
我平生最难忘的人
我母亲的形象如此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,以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似乎还认为每个老师都是她的化身。放学的铃声一响,我会立刻飞奔回家,边跑边想自己能否在她完全变身前赶回我们的公寓。可是毫无例外,每次我到家的时候,她都已经在厨房里,为我准备牛奶和饼干。然而,她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我停止妄想,反倒让我对她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更何况,没当场逮到她变身反而让我感到如释重负——即使我仍不停地努力。我知道关于母亲的本性,父亲和姐姐则全然不知,要是我在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撞见她,这种自我想象的背叛会压在我的肩头,这可是当时五岁的我所承受不了的。我想我甚至担心过,要是亲眼看见她从学校飞进卧室的窗户,或者看见她从隐形中四肢一点点显形,套着围裙,我大概会被灭口吧。
当然,每逢她要求我把白天幼儿园里的一切都告诉她的时候,我总是小心翼翼,乖乖照办。我不会装作理解她那无处不在的暗示,但是这肯定和她要搞清楚我以为她不在场时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有关——这一点毫无疑问。这种想象(以这种特殊的形式)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一年级,而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,就是我成了个诚实的孩子,因为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
啊,还是个非常聪颖的孩子。每次讲到我那位脸色蜡黄、身材过胖的姐姐,母亲都会说(当着汉娜的面也一样——诚实也是她的处世之道):“这孩子没什么天分,不过我们也不指望那种没影儿的事儿。愿上帝保佑她,她还算用功,尽了自己的力,所以拿什么成绩都没关系。”讲到我,她那埃及人长鼻子和能言善辩、喋喋不休的嘴巴的继承者,母亲则会带着她特有的克制说:“这个小土匪(1)?他甚至用不着翻书——门门功课都是A。简直是爱因斯坦再世!”
那么对这一切,我父亲又是怎么看的?他总是痛饮不止——当然不是像非犹太人那样干掉威士忌,而是喝矿物油和氧化镁乳剂。他嚼泻药,早晚吃全麦维麦片,吞下成磅的袋装混合果蔬干。他很痛苦——那真是活受罪——因为便秘而痛苦。她的无处不在和他的便秘,我的母亲从卧室的窗户飞回家,我的父亲读着晚报、屁眼里塞着栓剂……凡此种种,医生,就是我对我父母、他们的特质、他们的秘密所保有的最初印象。他常用平底锅煮的番泻叶,加上在他直肠里融化于无形的栓剂——这些就是他的法术:煮着脉络分明的脱水绿叶,用勺子搅动着这发出难闻气味的液体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倒进滤网,再顺着他那一脸的倦容和苦相,倒进他只进不出的身体。接着,他会弓着身子默默对着那只空玻璃杯,仿佛在等待远方雷声的指引,等待奇迹降临……孩提时的我有时也会坐在厨房里和他一起等。但是奇迹从来没有发生,至少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和祈祷的样子进行,好比撤销死刑判决、让鼠疫彻底消失之类的。当广播放送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,我记得他曾大声说道:“这也许管用。”但是对这个男人而言,所有的通便法都是徒劳:他的肠子被愤懑和挫败的铁掌紧紧攥住。而他妻子对我的特别宠爱,也加诸了他的不幸。
就连他自己也宠爱我——这真是雪上加霜。连他也看出,我身上蕴藏了使这个家庭变得“跟某人一样有出息”的机运,能让一家人赢得荣誉和尊敬——虽然在我小时候,他向我谈起他的雄心壮志时,绝大多数是就金钱层面来谈的。“可别像你这个蠢老爹——”他会一边这么说,一边和那个坐在他大腿上的小男孩开玩笑,“漂亮的娶不得,心爱的娶不得——要娶就娶个有钱的。”不,不,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被人瞧不起。他像条狗一样地工作——只为了一个他未注定拥有的未来。从没有人真正带给他满足,回应他适宜的善意——我母亲没有,我没有,甚至我那位可爱的姐姐也没有,他还认定我姐夫是个共产党(即便他现在已经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很赚钱的饮料公司,在西奥兰治也有了自己的房子)。而对他敲骨吸髓的,绝不是那个资产十亿的新教企业(或是像他们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“机构”)。“这是全美最乐善好施的金融机构。”我记得父亲这样声称,那时他第一次带我到他在波士顿与东北人寿保险公司的大办公室,去看属于他的、由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组成的一小方地盘。是的,在他儿子面前,他说话的时候带着“本公司”的自豪。当众声讨公司来自贬身价可说不通——毕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,他领的是公司发的工资,公司配给他的专用文具,那艘“五月花”号下面就印了他的名字(所以“五月花”号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标志,哈哈);而且,每年春天——适逢公司大发善心的季节——我父母还可以去大西洋城享受一个精彩的周末,不仅全程免费,连下榻之处也是称得上高档的非犹太饭店,在那里领受(连同大西洋中部各州所有突破年销——年度预销数字——的保险代理人一起)柜台人员、侍者、行李员的滋扰威胁,更别提那些一脸茫然的自费旅客了。
此外,他总是激情满怀地相信自己正在推销的东西,而这恰恰是另一个使他痛苦不堪、精疲力竭的原因。晚饭后,当他再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,踏出家门开始工作,他不只是在挽救自己的灵魂——不,他也在挽救某个放任他的保单失效,而连带危及了他家人“在雨天里”的安危的可怜混账。“亚历克斯,”他总会这么向我解释,“一个男人要应付雨天,就得备一把伞。你不能连把伞都没有,任老婆孩子挨雨淋!”对于那时才五六岁的我来说,他的话听起来大有道理,甚至令人动容,不过显然那些缺乏经验的波兰人、逞凶斗狠的爱尔兰人,以及住在贫困街区的黑人文盲们,对他的“雨天论”无法苟同,而“全美最乐善好施的金融机构”却总是派他到那些街区兜揽生意。